請還給我們,那消失在荒野記憶裡的「部落國家」!
老師要我們都捲起袖子,看看彎曲的手臂上是否有出現一道條凹痕。當時,我與鄰座的同學很篤定地說了沒有。巧的是我們的父系祖先都來自泉州惠安。那時我國中二年級。
回家後,我把同樣的問題問了阿母。她放下鍋鏟,捲起袖子,靠近手軸處顯現出一條明顯的凹痕,當時懵懂的我大聲告訴她這是有「平埔」血統的證明。現在只記得她告訴了我兩句話,成了我族群追尋的起點:
「我們有親戚住在埔里……」「小時候外公家有獵槍喔!他們都把它掛在臥室木門後方。」
從身體找回失落的記憶
小時候,我們坐公路局的車去東勢,在路上就會被說:「喔喔,是番仔囝仔喔!」
對於自小成長在豐原近山聚落的我而言,有親戚住在埔里這種空間上的區隔,令我印象深刻;而獵槍的故事,更是直接衝撞了那自幼築起的「漢人」認同高牆。被 baki(編按:噶哈巫語,「祖父」)帶大的我,小時候曾因看到表哥因台語不流利,而被叔公斥責為「外省囝仔」,如今卻從阿母那裡聽到:「小時候,我們坐公路局的車去東勢,在路上就會被說:『喔喔,是番仔囝仔喔!』」
如果不是回頭檢視那記憶的身體,以及從 baki 的口中聽到的那些故事,我只是一個走失在歷史迷霧裡的「漢人」。
認同、語言與祭儀的流失,讓我無法理解那分隔兩地親族們離鄉的道路!無法理解為何獵槍在阿母小的時候,被阿嬤賣給收破爛的人!無法理解,baki 一邊依稀所說的廣東祖籍,一邊卻在聊到客家人時以第三人稱的「他們」代稱!(編按:指祖父聲稱自己祖籍為廣東,卻以第三人稱稱呼同為廣東來的客家人)一切只有當我開始回頭質疑我的「漢人」身分與認同時,我才得以走上這條路。
聽過了前幾個世代不得不隱藏身分於漢人主流社會的我而言,如先行的哥哥姊姊們所言的,漸漸能體會部落主體與原民權利的重要性。我們已經失去的太多了。所以接下來請大家想像自己是一個剛擁有記憶身體的「族人」,要一邊面對殘破的歷史記憶,與當前嚴峻的現代國家體制和資本社會而來的挑戰。
請「國家」歸還,我們那本有而後失去的「權利」
身為族人,正名最基本的實質意義是希望國家知道,自己曾經做了些甚麼事。
首先,身為一個國家定義下的「平埔」族人,我想先由關於「正名」的問題切入。
對於我而言,「正名」是一個遲來的轉型正義。身為族人,正名最基本的實質意義是希望國家知道,自己曾經做了些甚麼事。我們有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、我們有自己固有的傳統領域、我們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儀式,這些都在歷史的洪流裡逐漸淡化、轉變。更隨著近代國家的移入,自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到戰後國民政府的占領,國家機器為利於統治,開始給我們戴帽子、給分類,以行政的手段告訴我們的長輩,你是誰,你不是誰!你的敵人是誰,你的歷史是甚麼甚麼(註)!
很顯然地,在原住民運動的過程裡,各社群領袖一直以來要求的,就是要告訴這個國家:
「嘿,有些權利,是在你們還沒建立時我們就擁有的,後來被你剝奪了。你來到了我們的土地。現在請你把這些權利還給我們。」
各地「平埔」族群部落的前輩、長老們也都以同樣的要求面對國家,然而至今這國家似乎還在昏睡。
在這個思考脈絡上,原住民族面對國家時所爭取的,切開補償正義的部分(指國家機器以暴力對人民生命、財產上的所造成侵害後的賠償,如二二八屠殺事件與白色恐怖。),剩餘的基本上,全都是我們本有「權利」的回覆。但這又遇到了一些問題:
我們的國家真的有這樣的決心嗎?
我們的記憶,是如何流失在國家與主流社會的潮流裡
國家公權力自始並未站在部落族人的立場,卻讓資本與開發主義的力量能更加速部落文化、歷史記憶、傳統領域的流失與崩解。
當我開始認同自己噶哈巫系的祖先,開始嘗試於以族名 Awui 作自我介紹時,在 2013 年的農曆年,我回到豐原老家請 baki 教我捕捉山羌與竹雞的陷阱。
一早他先帶我到北坑的山裡採了一些刺竹。本來我們打算在路邊就試做一個小型的陷阱,結果他對我說:「走,回家再做給你看!」。最後,他以紙箱為土地,教我做了陷阱的「模型」。
根據 baki 的記憶,家裡的獵槍在他祖父那一代仍時常使用,甚至遠至谷關狩獵,在山上將獵物烘乾、去除內臟後再帶下山來。直到戰後的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頒布,外來人口多起來後,獵槍的命運最終被交給了收破爛的人。
當各地的原住民族人以積極的態度,面對國家、面對主流社會大聲說出自己社群的歷史、自己的族名時,祖先圍獵的山林卻在《看見台灣》時才會被稍稍掠過一下;祖先採集的海岸,被水泥、鋼筋與波浪格板隔開。除了要面對國家,原住民族更被收編進了資本社會為發展的進程裡,而時常承受主流社會所排除的外在成本。
2010 年,台東縣政府及台東市公所以「都市發展及發展觀光產業」之名,在沒有任何討論及通知的情況下,將第六公墓由公墓用地改成了農牧用地,更要求第六公墓及第十公墓(位於加路蘭部落)在期限內遷葬,以便興建公園。
第六公墓是日本時代,日本殖民者為了改變卑南人室內葬的習俗,將卡地布部落族人埋葬於祖靈屋 karumaaan 的骨骸,統一集中安葬之所。該公墓位於部落南北通路的要衝,族人將祖先遺骸中安葬於此,希望祖靈繼續看顧後人。然而為了發展,台東縣市政府卻無視《原基法》的規範,以一紙公文要安居於此的祖靈流離失所。
在卑南人的慣習裡,會將亡故的親人埋葬於屋內,直到屋內墓穴安葬滿親人遺骸後,將其作為祖靈屋。karumaan 在卑南語裡為「固有的家、真正的家」的意思。不管家族遷居、新建房屋於何處,karumaan 是這整個家族的根源所在,也是儀式、文化傳承發生的場所。
在這個例子裡,國家公權力自始並未站在部落族人(也都是有納稅的「中華民國國民」)的立場,卻讓資本與開發主義的力量能更加速部落文化、歷史記憶、傳統領域的流失與崩解。
當我們選擇積極面對國家的不作為時,還要面對來自資本、發展主義的挑戰。我們應該如何更有力的實踐祖先代代傳承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呢?
部落,才應該是我們的「國家」
少了「部落國家」的保護,族人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,成了毫無抵抗、被解除武裝的「弱者」,一切只能從頭學起。
距今一百多年前出生於阿里山樂野部落的鄒人先行者 Uyongu Yatauyungana(漢名:高一生)已經先幫我們想到了辦法:原住民自治 -- 但卻也因他提倡的「原住民自治」不見容於中華民國政府,於 1954 年遭以「匪諜叛亂」罪名遭槍決。
有統計數字顯示,全世界至少存在有四億的原住民族人口,而這麼多原住民族各社群固有的歷史脈絡、文化慣習、傳統領域,以及構築其上的社群關係與社會組織,是不能簡單地以現代國家的機制或法理制度的框架去討論。至少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裡,原住民族各社群的存在,非常明顯早於這個戰後才移植來台的「國家」。
換言之,現代國家的機制或法理制度這些框架,並不能漠視或排除我們本有的「權利」。
國家的移入就像一個蓋子,把我們全部都給蓋住。國家機器(例如主流教育、國有地劃定、強制遷村)與現代性(例如貨幣經濟)強烈地侵蝕著我們文化與社會機制的根基。把時間往前推,以中部最早與清帝國接觸的岸裡大社為例:清帝國在進入部落初期,便建立起了一套有別以往長老會議的部落領袖遴選制度,從中培植願意與之合作的部落領袖。近代國家更以多重手段弱化部落的機制,使得原本的部落組織逐步崩解。
少了「部落國家」的保護,族人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,成了毫無抵抗、被解除武裝的「弱者」,一切只能從頭學起。
從老人的口中,可以想見「現代」是如何直接地介入、影響以往所熟知的生活。在今年夏天一次和 baki 聊天的過程中,他給了我一個例子:baki 曾祖父的墳墓,在那個世代,baki 的 baki 家人還沒有漢人二次葬的習俗,那個石頭壘成、沒有墓碑文字的傳統墳墓,最後湮沒在石岡水壩附近的公墓裡。「神聖性」倉皇地從歷史的洪流裡退位,快得讓老一輩的人們還來不及反應;熟習的生活也與失去的獵場、記憶遠去。然而那個濃厚的氣息仍瀰漫在山野裡與 baki 的故事裡。
過了幾個世代,如今我們卻仍面對著相同的問題。年代久遠地連 baki 都已快忘卻陷阱獵的作法,而獵槍更早已在阿母童年的記憶裡退場。
積極地跟這個國家要回我們失去的種種,回復我們的「部落國家」、回復過往的機制,才是我們得以活得像個人的方法。先有了文化、歷史脈絡與權利意識的覺醒,接著將要導向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實踐。也許我們得花上兩三個世代的時間,然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還我自治權
對我而言,理解、想像中的「自治」,已等同於今日現代國家定義下的「獨立」了。
復振弱化的「部落主體」,連結了前面討論族人面對國家時對自身權利的覺醒、面對資本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參與實踐,而後導向文化、生活的落實。因為在跟這個國家交手超過半個世紀的今天,我們早已失去了許多珍貴的人事物。
所謂的「部落主體」是包含了過去部落所形塑的對外、對內各種機制的集合,是保護部落內部延續以及與外部達到折衝、結盟的整體。如今,主體的復振,讓我們的人得以更有準備地向外面對這個國家與資本社會。自治的實踐,在法理上是對我們原有權利的回復與肯認,例如傳統領域的自然主權。再一次回響:原住民族的問題,需要回到部落主體,我不認為可以完全由西方社群理論(政治學或社會學)的觀點來討論部落內外的種種,更不能以現今國家框架下所主導的政策制定的角度去談論。
如何在今天國家所主導的「福利」政策下,取得族人的理解與認同,並在體制內外逐步落實「自治」,實在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對我而言,理解、想像中的「自治」,已等同於今日現代國家定義下的「獨立」了。唯有如此,我們才得以在這個艱難的時代實踐祖靈的教導,看顧祖先曾行走的山野、祖先所說的話語、祖先的技藝與舞步。
2013.12.22,於 擺接社故地
註
- 補 2013 年公聽會資料裡公文稱「平埔」與原住民互為「他者」,殊不知這個他者也是清帝國植入以後才開始出現的分法。是否泉腔的河洛人也稱漳州人為他者?布農也稱賽德克為他者?
相關文章推薦
想隨時看更多原住民的新聞和故事嗎?
現在就加入我們的粉絲團吧!
圖片來源:《Mata‧Taiwan》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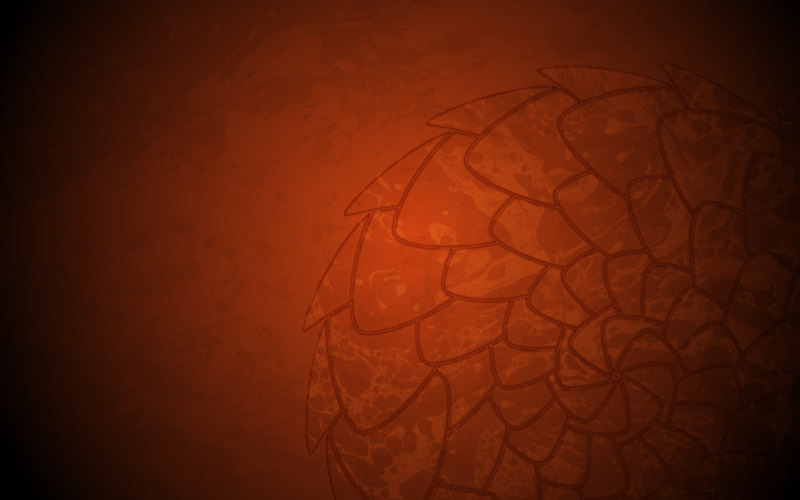


Leave a Reply